读书会|谪仙人的海外旅行:读哈金《通天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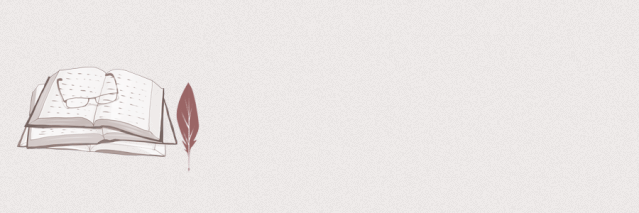
文学观澜·读书会中国作家网从全国高校、社会团体的线下读书会出发,集结文学爱好者,聆听文学声音,传递文学思想。无论是新作锐见、好书推荐,还是经典重读、话题讨论,跃然于纸上的都不只是凝固的文字,更是跳动的思维。文章形式多样,既可以是探讨,也可以是评论。欢迎更多的读书会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线上线下,尽情碰撞。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方式。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蒋洪利 “通天”译名的多种面相《通天之路:李白传》原著名为 The Banished Immortal: A Life of Li Bai,其中“The Banished Immortal”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被放逐的神仙”或者说“谪仙”。然而,作为一本面向中国读者的李白传记,如果再次译为“谪仙”则毫无新意。所以,译者将其译为“通天之路”可能有为市场考虑。然而,如果单纯地认为书名的选择是满足读者的猎奇以及迎合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就低估了译者的真实意图以及书名所承载的多重意蕴。《通天之路:李白传》作者: (美) 哈金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译者: 汤秋妍出版日期: 2020-2首先,“通天”可以理解为“入仕”或“进入庙堂”。李白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直在为如何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而努力——他渴望自己的政治见解与政治能力能够直接得到君王认可。所以他对小官职位不屑一顾,一直渴望通过被人举荐或自我干谒的方式实现“一步登天”的政治理想。所以在这里,“天”除了有政治功业的意味外,还暗含着李白想直接辅佐皇室的理想。哈金在《李白传》里的叙事脉络也一直沿着李白在追求仕途中的挫折与磨难、成功与失败展开。就此而言,“通天之路”即是李白的“入仕之路”。其次,“通天”还可以理解为“到达天人合一”。在李白的思想构成中,除儒家思想外,道家思想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李白性格中的狂狷、随性自由有着道家“道法自然”的影子。在李白的一生中,他不仅拜师修道,还曾多次求仙访道,身体力行地实践着道家的思想与精神。如果说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的话,那么,李白在对道家思想的求索中也试图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通天之路”即为李白追求道学精神最高境界之路。在李白求仕的过程中,他曾写过很多展现自己文采、政治思想,歌颂干谒对象的诗作,这些诗作本是他借以赢得他人赏识的工具,但仕途的失意让这些诗作失去了自身功利性的价值。反倒是波澜起伏、跌宕丛生的人生际遇催生了李白诗歌的创作热情与创作活力,使其创作出了许多内蕴深厚、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歌作品。当手段本身成为目的的时候,李白在入仕和求道之外找到了另外一条通天大道,那就是诗歌创作。李白以其雄奇的诗才、敏锐的感受和灵动的艺术表现力创作了一首首堪称精品的诗作,而他本人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伟大诗人。在我看来,译者汤秋妍之所以将“谪”改为“通”,将“降序”改为“升序”,是因为她看到了构成李白人生的种种矛盾关系,而这也是哈金在结构和撰写《李白传》时所意图呈现的生命张力。应该说,我们只有在真正理解文题的丰富内涵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李白的人生以及《李白传》的写作。反过来说,只有细致而深刻的感悟《李白传》的写作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译者在文题上的良苦用心。田雪菲 李白的“吟游”之途哈金笔下的李白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欧洲特殊的文化群体——吟游诗人。尽管中国诗歌自古也拥有“游”的文化传统,诸如孟浩然的“田园之游”、杜甫的“壮游”、王维的“边塞之游”等等,但西方“吟游诗人”群体身上丰盛的想象力与创作力,冒险的英雄精神,可歌可舞的浪漫情怀显然与李白的个人气质十分契合。也因此,“吟游”体验或可成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李白的另一种视角。传记写作中,哈金富有层次地营构了李白一生的“吟游”体验,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其一,李白一生好以干谒,他将自己的诗作视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因此不得不周游四方,广泛结交权贵以寻求机遇。其二,作为“永远在路上的旅人”,李白每到一地都会作一停留,也因此不断汲取“地方”“民间”元素来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如他到江陵学习楚风民歌作《荆州歌》,到东北幽州兵营为边防战士作诗(《出自蓟北门行》),以及后来目光“下移”,不断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丁都护歌》等);其三,随着李白的诗名远扬,他也会被上层官员邀请宴席,为主人们即席献诗,歌功颂德。如李白在邠州时,住在邠州长史李粲家中,日日即席作诗,极尽赞美。进入翰林院后,他跟随玄宗前往骊山游行,歌咏骊山盛景,赞扬贵妃美貌;其四,李白在政治谒游以外,也常前往全国各地拜访好友,在与友人们的唱和中充分抒发自己的诗情与才情。如《将进酒》这一传世名篇正是在与元丹丘、岑勋的纵酒狂欢中创作出来的。漫漫一生的“吟游”之途烛照了李白落拓不羁的精神风貌与才子品性。李白因出身卑微,极度渴望加入王室来改写命运,以证明自己的杰出与不凡。也因此,他唯有在辗转的旅途中才能广泛干谒,实现理想。其次,李白不受拘束的性格注定他只能是在外的流浪者与漂泊者,即便他多次组成家庭也无法停下漫游的脚步,这正显示了一个诗人生命的本质——孤索、自由、桀骜。当然,李白天然浪漫、多感的文化心性也是他能够吟游一生的不竭精神动力。在“吟游”视角下,哈金将李白的个人追求、创作历程与精神风格紧紧胶合、互渗,最终展示出的是对李白“身份”“创作”与“风格”三位一体的记述。胡婧 多元视角下的李白哈金在开篇就明确了写这本传记的一大目标:他想要尽可能多地呈现“历史真实的李白”。所以,在《李白传》中,作者一方面试图通过李白的诗文与行迹探寻他内心的想法,另一方面借由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下的群体视角,让我们看到李白在官场、友人和家庭中呈现出来的三重面貌。在高官大吏面前,我们看到了一个渴求功名的李白。他呈上华丽的赋、明快的民歌;他在宴会上即席赋诗,向众人展示他下笔不休的才华。人们最初都被他的才华打动和吸引,但细细考量,又顾虑重重:他是商人的后代,出身卑微;有些奇技杂学,会点医术就到处给人诊病,会点剑法就想当个军官;嗜酒成性,酒后举止轻狂傲慢,与三教九流混迹一处,不是个稳妥谨慎、能堪大任之人。但是在另一群不那么得志的小官面前,李白恰恰能与他们惺惺相惜。他们摆脱了政治制度里的上下级关系,以平等的朋友关系相处。在同样出身低微、毫无架子的人面前,我们看到了更加轻松自信的李白,他的乐观天性和理想主义流露无遗。这些朋友更加愿意向他倾诉心事,吐露官场复杂的一面。这本传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哈金关注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女性视角。李白因为出身低微,非常看重女方家世,两次入赘。第一任妻子许氏是湖北的大家闺秀,在结婚的12年间,李白常年在外,两人聚少离多,她一直迁就与忍让着丈夫。父亲去世时,李白仍在外地,许氏分不到家产,只能守着几亩薄田苦苦度日。生下女儿不久,许氏身体抱恙,还未完全康复就得听从李白的决定,举家迁往山东。第二任妻子宗氏,欣赏李白的才华并想与他一起潜心修道,可李白仍摆脱不了对功名的渴望。和上一段婚姻一样,他一意孤行继续四处奔波,增添了妻子的思念与担忧,最后也未能达成所愿。安史之乱以后,因为投靠永王,李白被流放夜郎。发配前还靠宗氏与其兄长打点官兵,才不致过于狼狈。哈金对李白人生脉络的讲述是贴近现代读者的。借助流传下来的事迹,哈金着重刻画了官员、友人与妻子这三类人和李白在一起的感受。这样的描摹恰恰符合现代人最熟悉的三个场景:工作、生活与家庭。哈金从这三个方面出发,用现代生活的思维框架为唐朝的李白画了一张素描,展现了一位普通人也能读懂的李白。这样的视角无疑拉近了我们对于李白的认识,李白的形象也启发着现代的我们。战玉冰西方现代传记视角下的《李白传》哈金的《李白传》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写的虽然是中国古代人物,但写法上却基本依循了西方现代传记的书写范式。其基本特点是:一、在基本遵照历史材料的前提下,允许部分细节的虚构;二、将心理学引入到传记写作之中。从第一点来看,会涉及传记作为一种文类要如何进行理解和把握的问题。简单来说,传记是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一种文类,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提出的“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更是从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确立了传记自身的文类特色与价值。在这一认知基础上,西方现代人物传记一般来说需要遵照起码的人物生平历史材料与主要事件的真实性,同时允许部分的、适度的细节虚构,而这种虚构不能和已有的公开历史记录相违背。比如,哈金在《李白传》中写到李白与骆宾王惺惺相惜,并在骆宾王死后“专程前往骆家村里骆家的老土坯房,在他的衣冠冢旁静默哀悼。又在他家附近的水塘边,喂食了几只水鸟”。后者显然是哈金自己的文学想象,其想象的基础是骆宾王7岁写出《咏鹅》诗。换句话说,哈金在这里所虚构的李白悼念骆宾王后去水边喂水鸟这一细节,分明暗含了向骆宾王《咏鹅》致敬的意味。当然,我们无从得知李白当时是否真的去投喂了水鸟,或者我们还可以大胆判定李白即使要追忆骆宾王的文学创作也绝不会找他孩童时代的这首“游戏习作”,而是应该会致敬骆宾王创作成就更高的七言歌行体和那篇著名的《帝京篇》。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李白传》中这样一处有意味的细节虚构显然更能引发联想,联想到李白怅然若失地在水边投喂水鸟的孤单身影与落寞神情,同时耳畔回响起每个中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即是莫洛亚所说的写人物传记要“从他伟大的一生中突出具有小说情趣的内容”。从第二点来看,自从茨威格将心理学引入传记之后,试图通过揣摩和把握传主心理来结构和解释其一生经历就成了西方现代传记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具体到哈金的《李白传》,我们会发现,作者很善于抓住李白的一些内心情结来作为把握其生命选择和人生行为动力的关键性因素。比如书中塑造李白“想做官”:“经历了数十年的挫折和失望,李白还是同一个人,他的思想和人生观丝毫没变。他仍梦想上朝堂、辅君主、建立伟业,然后功成身退,成为传奇。”这是贯穿整本《李白传》的一个重要心理情结,为此他娶相府之女,不惜两次入赘,“李白的整个生命似乎都被贵族身份强烈吸引”。又如李白年轻时曾看到崔颢的《黄鹤楼》而“甘拜下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而哈金在写到李白晚年创作的《登金陵凤凰台》时,则将“长安不见使人愁”一句视为对李白一生念念不忘的“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某种回应。而这背后另一层隐含意义在于李白通过这首诗的创作,表明自己在乐府、歌行和绝句之外,在七律的创作上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而这种文学成就的突破与取得是与某种被哈金建构出来的人物心理情结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对于一本偏文学性的人物传记而言,这种对贯穿人物终生的“心理情节”的把握会使得整本书非常好读,给读者一种专注生平的整体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李白传》在努力地从内在的、心理的角度把握李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面向,比如李白的一生经历了盛唐到中唐的时代转型,而这一由“安史之乱”所引发的时代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唐诗的创作风貌与精神气质,也是李白晚年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李白传》在积极构建李白内心世界和个人主体特质的同时,在这一方面或许还有所不足。
文章来源:《国外文学》 网址: http://www.gwwxzz.cn/zonghexinwen/2021/0707/592.html